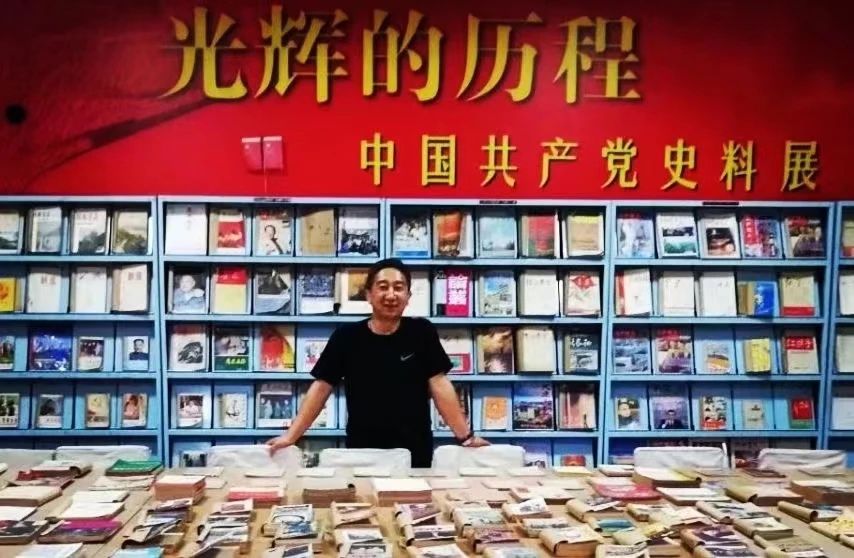暮色慢慢深沉,喧闹了一整天的城市,渐渐进入了梦乡。忙碌一天后,终于可以躺在床上了。打开手机,一则征集“白银最美读书人”全民阅读先进典型事迹的通知,出现在屏幕上。
最美?我肯定算不上。但是,读书人,应该可以沾点边。夜深了,月色朦胧,万簌俱寂。难得的雨后晴空,天空似乎离人间很近,为数不多的星星缀在蓝缎子般柔和的天幕上,悠悠又幽幽地发着清冷的光辉。这丁香花盛开的春夜,久久撩动着我的心扉。
人的记忆一般从几岁开始?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好长时间。有一种说法,大多数人的最早记忆始于三到六周岁,如果晚于六周岁,那是极端现象,可能存在严重智商缺陷。
而我最早的记忆时间,已是七岁的年龄了。为此,我便将自己定义为愚笨者。
七岁那年秋季,连绵的秋雨之后,我家的老院周围都是水,如同涝池一般。不知道是哪一天,村里的学校开始报名招生,看着哥哥姐姐们都在整理书包,我站在正给院墙周围排水的父亲边上说:我也要读书。
在这段记忆画面中,再没有其他情景,后来我就背着书包上学了。那个年代,并没有入学年龄的限制,大多数孩子都在八岁之后才上学。因此,我成了村学里年龄最小,而且是唯一穿着开裆裤上学的学生。
我的小学一二年级是在我们自己村里读的。那时候,父亲在外地教书,母亲在家里忙碌。放学后,我大多会在教室里写作业,母亲会牵着我家那匹骡子到校门外,喊上我一声,然后我再牵上骡子到村外的涝池去饮水。等骡子喝饱了水,我就骑着它,晃晃悠悠地回家。
在村学读书的时候,并不知道用功,常常都是趁老师不注意,和伙伴们到学校外的院子里玩自己喜欢的游戏,而所读的书本,半学期之后,就会从中间一折两半,如同小人书一般。上课时,只能拼接着用。但是,期末的成绩似乎并不是太差,甚至“名列前茅”,偶尔还会被唯一的老师夸奖几句。
等后来我读到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时,便倍感亲切,感觉先生就是照着我的生活在书写文章。我也因此对先生特别崇拜,后来到师范读书时,甚至在一笔记本内专门绘制了“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之位”的牌位,以示尊重。再后来,还曾写过文章《撕开脓疮撒药的男子汉——与鲁迅的心灵对话》,参加纪念先生的征文活动,获得全国二等奖。
三年级以后,就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读书了。
乡里的中心小学距离我们村有好几里的路程。我们每天都是走着上下学。夏秋天还好,冬春季就比较麻烦,特别是早晨,天还没有亮,就得走路。我们同村的几个同龄人便相约在一起,摸黑前行。
因为年龄相仿,很多事都能够共同完成,唯独读书不是。有几天,恰好语文老师要求我们背课文,于是大家就商议,趁着早上走路的时候顺便背会课文。但是,天黑的时候,几乎什么事情都无法完成。有人提议,每人背一部分,再领着大家背诵。原始而纯朴的小组合作式学习,便在我们身上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践。因为每天的时间很充裕,不知不觉中,语文课本中的课文差不多都被我们背会了,甚至连《鸡毛信》《猎人海力布》等不要求背诵的长文,都烂熟在心,真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现在想来,最简单的方式,或许是最有效的方式。
因为学校离家里较远,加之大人都忙,所以我的小学中午时间大多在校园里度过。除去炎热的夏季,我们几个小孩子一般都不睡午觉,经常玩的游戏也会变得无趣。好在我们村里有一个小卖铺,这里出售日用百货外,也租小人书。记得当时每本小人书的租金是一天五分钱。可以前一天放学后租起,第二天放学后还回。我便将所有的零花钱都积攒起来,以供其用。
大家通常是你凑一分,我凑二分,然后共同享用书册。因为课堂上不敢看,害怕老师抓住没收,所以只能在中午或者晚上放学后看,有时候也为了和别人换书看,往往时间紧张时,大家都是挤在一块共同看。这段时间,《武松打虎》《岳飞传》《烈火金刚》《薛刚反唐》等等,都让人欲罢不能。
小学五年级毕业,我竟然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中。暑假里,父亲给我一本厚厚的书,书名叫《欧阳海之歌》。书中写战士欧阳海从一件件小事情做起,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,关心别人,不计个人得失,表现出穷苦孩子早当家的吃苦耐劳的光荣本色。特别是最后,部队野营行至铁路边时,驮炮的军马受惊吓,站到铁轨中间任凭推拉都不离开,欧阳海眼见远处火车已经驶近,毅然冲上路基,奋力将军马推下路基,自己却被火车轧死。书中的情景至今都留在我的脑海中。
读初中时,认识的字多了,小人书渐渐淡出,阅读的大部头书籍也渐渐增多。武侠书籍诸如《雪山飞狐》《血刀老祖》,历史人物故事诸如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演义》,都会在闲暇时如饥似渴地去读。说起《隋唐演义》中英雄好汉的排名,使用的武器名称、重量等等,比起课本的内容来,不知道要熟悉多少倍。有时候,还拿不同书本中的人物相比较,让关公战秦琼,然后分析优劣输赢,往往不得答案,几个人讨论时,也争得面红耳赤,不欢而散。
初中毕业,我考入靖远师范学校,这是一座以培养小学教师为主的中等专业学校。
生命的行进与流逝应该是汹涌澎湃的。可是,闲暇的无聊和单调的苦闷常使我无所适从,我的灵魂向我宣泄的,永都是孤独和寂寞。
师范以艺术培养为主,在校的时候,我把太多的时间交给了音乐课。那些时光,我所在的音乐班,每周两个早自习练习视唱,两个晚自习练习弹琴,每周有八节音乐课。几乎每天都冲在抢琴和练琴的路上。琴房的对面,就是学校的图书馆,琴练不下去了,或者无聊时,也会躲入其中,翻翻书籍。
后来,图书馆不知为何不让随便进入,只能在窗口外借书,然后拿回宿舍阅读。为了撑面子,不时也会借上一两本。可能是早前形成的阅读习惯吧,我看书总比同宿舍的学友们快。他们借的书,往往都是我已看完,他们还在计划中。这样,三年的时间,居然读完了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整部小说。《红楼梦》则是硬着头皮,也没有完全读下来。至于武侠小说,一直都是情之所钟,自不用说了。
师范毕业那年,我十八岁。十八岁,正是活人的时候,我却被分到了煤矿,给一群被侃称为“矿匪”的孩子当老师。那里山大沟深,通向山外的有一条公路,还有一条运煤的火车道。山上倒还有几棵树,我戏称之为“深山老林”。
在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,用心捧着英气荡漾、豪情万千的理想走来时,却要为人师表。单调和寂寞,平静和贫困。黑板、粉笔,课本、学生,日日轮回,月月相依。我迷茫,但在迷茫中仍然读着生活。迈入社会,才真实体验到了挣钱的艰辛和做人的艰难。也许,这才是人生的第一步。
矿区的黄昏比清晨还要美好。落日又大又红,慢慢沉落间,似乎在尽力挥洒着自己的余晖,把苍山都染成了金黄。等到夕阳落山时,那苍山的轮廓上,便镶上一道血红的花边,极为肃穆庄严。但在这肃穆庄严中,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哀怨和悲壮。
在煤矿子弟学校,我买的第一套书是《平凡的世界》。书中的孙少平从贫困的农民家庭走出来,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,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。井下的黑暗作业,带给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劳累,还伴随着生命的危险。但他那坚毅勇敢、积极向上的品格,那份对生活不低头、不服输的坚韧内心,那份热爱生活、渴望知识和期待未来的饱满精神,都成为我学习的楷模。
深沉的夜色中,传来的是粗犷又婉转的秦腔曲子,使人沉醉却又自失。当晚风凝聚幻想的灵光,抚摸着,抑或是敲打着,犹如呼哨般穿过我的身体时,我不禁浮想联翩,感慨万分。在这满天的暮色里,心里总涌出一种难言的感情。我的理想,我的追求,我的灵魂,就像一尊黑色的塑像,伫立在那里久久地凝望着……
每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都在读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我同情孙少平的青年时期总是与苦相伴,但我能读到他在每一次转折时,都会走向更大的人生舞台,我还能读到他和考上师专的田晓霞那荡人心肠的爱情。
生活,从来都不是平静的,追求与渴望常伴有强劲反弹似的矛盾。我曾埋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,兢兢业业却不被社会尊重。也曾埋怨工作环境太差,起早贪黑却默默无闻。但更多的是,始终如一站在讲台上,长年累月爬行于厚厚的作业本上,在如饥似渴的目光中解疑释惑,在天真烂漫的花从中教书育人。
时光流逝,不时听到我的校友中有人自学考试合格,拿到了专科文凭,还在自学本科课程;其中不乏硕士毕业,更有的在攻读博士学位,著书立说;有人名于“优秀教师”、“教学骨干”之列;有人当上了校长,局长或经理;虔诚地去参加一次隆重的观摩教学,走上讲台的竟是昔日的同窗……
稀疏的星子,明灭于迷蒙之夜。泪眼蒙眬后,不再是心灵的抱怨。沉重而又令人烦恼的生活被抛到了身后,新的陌生的岁月不断地接纳我。大山,包容了一切的苦难和泪水。透过夕阳,一切沧桑与磨难都是淡去的轻烟。当我的学生小学毕业时,我取得了大专文凭,而当我的学生初中毕业后,我也再次踏上了省城的求学之路。
黄河之畔的教育学院,是淬炼人生的八卦炉。
课余,我常常一个人看夕阳。远山已经朦胧,西边河头的夕阳又红又圆,静谧的黄昏无声无息。那如血的夕阳慢慢地落下去,只留西天一抹金黄的霞云。待到浑黄的河水泛出金光时,我知道,夕阳终会隐去最后一抹余晖。虽然,我还在痴痴地看。
我也常常站在古老的黄河边上凝神沉思,一个小时,又一个小时,一动不动地欣赏东去的河水。黄河,流泻着一切坎坷与痛楚;黄河,消融了一切苦难和不幸。他流动不息的是宽容一切、奔涌向前的生命,他迂回不止的是关怀一切、博大深情的慈爱。他拒绝别人的赞美,拒绝别人的夸耀;他拒绝别人的安慰,拒绝别的人同情。他带着他的自尊,他的自省,他的自爱,他的自强;他带着他的浪涌,他的涛声,他的泥沙,他的风采,威猛地流动着,乘着长风,飘向遥远的天际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中,田晓霞为了救人而牺牲,带给孙少平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。据说这部巨著的创作者路遥,在写到田晓霞去世之时痛哭流涕,不能自已。我读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故事,实在想不出怎样让他们收获完美的结局。这段梦幻般的爱情故事,或许是我们大多数人心中爱而不得的忧郁情怀。无论是煤矿山巅,还是黄河之滨,我也多次潸然泪下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,成为最为打动我的著作,没有之一,至今还是。
岁月有流程,永远无止境。沿途的风景,看过了,也就越过了。转瞬间,当我在古老的黄河之滨苦读两年之后,才发现梦很长,路也长。虽然有千行眼泪,有百转柔肠,可人毕竟不是靠他者发光的月亮。时光,磨炼了人,也造就了人。
连同教育硕士阶段在内,我在师范院校一共就读十二年。早期读的书籍,不少历历在目,后来所读,却是越来越淡忘。于是,收藏书籍,渐渐地代替了阅读书籍。更多的时候,手机阅读,成为主流。
岁月交替,致力于乡邦文史的研究,地方文化的宣传,为更多人提供读书的机会,逐渐成为我教书育人之余的重要工作。倡议创建瞭高书院,协助成立白银市作家专柜,帮助他人校对书稿,或许,这些都不值得一提吧。
读书写作,依旧清贫,依旧淡泊。然而,心给了这片土,所有的心血就在这里倾注;人给了这片土,所有的爱都在这里投入。泪水中有欢颜,辛酸中有成功,正如已习惯于被称作“老师”一样,多少次孤独,多少次期待,都在这里融化了。夜深时,仍在读书,仍在写作。在这里,只有开始,没有结束。
作者简介:
王承栋,男,笔名大漠孤剑,教育硕士,中学正高级教师。甘肃省学科带头人,省级骨干教师;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,白银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在省市级以上报刑发表诗文百余篇(首)。
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